蓝天白云,小时候隐隐约约记得是有这个词的,但给占据画面一半的天空上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劣质的水彩笔的墨水一定是经过偷工减料,18色的一箱水彩笔里,最先用完的总是蓝色。每次给妈妈说我的水彩笔蓝色用完的时候,她总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脸上写着“这才过了几天啊”,我拿着背面也渗满墨水的纸张给她看,她先是例行公事地夸赞我的惊人的创造力,随后再说一句“就是太浪费蓝色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水彩笔的蓝色总给我一种很不健康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刺鼻的气味总让我联想起医院的消毒水。(虽说消毒水是为了健康而存在的,但它总是在会聚集不健康的人的地方出现)。其实其他颜色也未必健康,但因为常用到蓝色,因而格外介意蓝色。久而久之,总觉得连通它的色彩一起觉得“不健康”起来了。那种蓝色说不上来,但在自然界里我还没见过,蓝天首先并不是那个颜色,但我的工具有限,只能拿它来示意老师“我理解天空是蓝色的”,不至于被当成被色彩弄迷糊的小笨蛋。但心里总觉得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是得要找到更健康的颜色来替代它,二是要不然还是不用蓝色来画天空了吧。
于是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画里尽是蓝云白天。再也不犯愁水彩笔的墨了。老师在课后把我叫了过来,问我为什么要把云涂上蓝色。我背着手在身后,思索着这个理由是不是足够充分,然后挺直了胸像是自己从内往外拍了一掌似的,说这是我发现的新的艺术表达手法。刚工作没两年的美术老师的长直发随着凝结的空气耷拉在肩膀上,随后她爆发出了让窗外的树枝都摇摆起来的笑声,窝坐在比我还高的椅子上的她缩成了一个团子,过了几秒她才整理好心情,摆出给小孩看也可以理解的表情:大概就是非常慈祥与带一些“逗小朋友”的成分的笑容,然后给我说:“这样不错嘛。”
可惜先前只是蓝天不够健康,现在白云也被我染蓝了。整个天空都显得不健康了。我呈大字型看着窗帘外的既不算蓝也不算白的天空,飞机场离家里不远,高楼也不在窗户的近处,于是我每天都能看到拖着长长的白色的尾巴的飞机在天上画各种线云。这就像小时候用铅笔打的草稿没被擦掉,又立刻用水彩笔上色了,于是水彩笔的印子下面有着再也擦不干净的灰色线条。不好看,没意思,而且,有一点不健康,让我想起来了水彩笔的味道。看这样的天,就算是买了96色的水彩笔,也没有画下来的兴趣。
我以此为借口赖在了床上,等到阴郁的乌云一点点飘过来遮盖住原本的铅笔印子,窗外也有了雨的声音。因为窗户的存在,这个世界好像离我也不太近。床像是失去意识的史莱姆,用本能把我包裹在柔软的身体里,我则是昏厥的睡美人,因为还没有听到王子来的声音,睡觉又不是随时都想睡,而醒来又很无聊,万一装作睡觉被人发现醒着又很麻烦,所以我像是在躲避哨兵的监视一样时不时的睁眼看一看窗外的世界,然后又陷入自己的脑内战争;等无聊了,再看看窗外。虽然一般的普通人类也不会透过我六楼的窗户翻进来,王子也不可能。但这也是我和另外的世界为数不多的联系了。
再听到雨的声音的时候,我在家外面做着漫无目的的散步。
隔壁刚刚放学的初中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不知道从哪儿的小道里穿越回了家,一个健步把书包投掷进了半掩着的家门,妈妈没发现儿子没有进家门,但家里却有“咚——”的一声,随后闪进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如果妈妈还在厨房里做菜应该会被油烟声盖住吧,如果是在客厅里看电视,恐怕是会被吓一大跳。初中生转身说了句“不好意思,借过”就从我的身边以同样的速度飞了出去。在转角的路口有几个同样校服的男生徘徊,估计是放学了约好去打球之类的吧。年轻真好,这句话还没等我说出口就觉得有些太装着像大人了,于是又咽回了肚子里。我光顾着看眼前的光景,忘记了用自己的脚从楼梯上走下去。
这时候已经有一些像是别人没晒干的衣服从窗户外面的支架滴答在我身上的感觉了。最初被叮到的总是脑袋,头皮上的细胞有时候比我预想中更敏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秃头的征兆——本应该有头发覆盖的头皮的哪里变秃了。我摸了摸脑袋,却没能抓到雨水。穿着短裤短袖出门的我似乎早有准备,虽然没有带雨伞,但穿着的也是进水也没关系的凉拖。我不喜欢夏天的闷热的感觉,索性下一场凉快的雨也还好,但如果是那种顶着大太阳下的雨,不仅湿度很高,身体还像是泡质量很差的温泉一样,被雨渍包裹地浑身难受。看起来篮球少年是不能如愿了。
风打在树的叶子上,啪嗒啪嗒的声音,让人以为雨已经变大了,但其实只是风而已。这时候的风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但我还是不争气地打了个喷嚏。本来的计划是出门就算胜利,但现在双脚都落在了被雨淋成斑点狗的水泥地上的我应该已经算是卫冕冠军了。既然如此,就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好了。门口的共享单车平时总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但现在却还有几辆剩下的。屁股无论如何都会被硌着,所以最普通的一辆就好。我的身高比上一个乘客要矮不少,花了不少时间摆弄了座椅,终于调试到了合适的高度,却发现二维码被黝黑的马克笔涂抹过了。我顿时想起来了:马克笔好像是比水彩笔更伟大的东西,我为什么不买蓝色的马克笔呢?
出行的计划浅浅地泡汤了,但马克笔确实很不错。我沿着门面店那一排排窄小的招牌向文具店发起进攻,招牌与其说是挡雨不如说是雨水的引流器,哗啦啦地往地上泄水的不是挂的高的那些散发着危险气息的乌云,而是近在头顶的小店招牌。招牌和招牌没能紧密的贴合的地方,我准会被淋一个头。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确实秃了,那强烈的触感比用手触摸还要强烈不少,像是直接用受伤了还没长好皮肤的裸露的伤口。痛啊!我一手挡在头顶,一边加快了走路的速度。结果迎面撞到了一个拿着半个包子从包子店里出来的人,原来是包子店的老板在偷吃。包子被我撞飞到了雨地上,沾上了灰黑色的泥水。老板的神情显得比我还忧郁,我的“不好意思”“对不起”“非常抱歉”怎么也不能说出口,因为看到他那副失去包子的表情就像是我当了个杀人犯,于是我就像是逃犯一样撇开了话题,“不好意思,这包子陷可真多啊,老板我要买一笼。”道歉还是先说了,不然老板可能真的会反杀我。
晚饭总算是有着落了。不过这倒是意料之外。睡到这个点别说是晚饭了,早饭午饭自然是完全没吃的,虽说在家也有的吃,但在家快要发霉了,好像就不能进入这个世界了。我就像到了晚上还没做日常任务的人一样冲了出来。这样出门的时候怎么能想起来晚饭呢?但晚饭就这样无中生有了。
我从淋过雨的塑料袋里掏出来一个冒着热气的淋过雨的水灵灵的包子边走边吃,拐角的文具店意外地有伸出脑袋的雨棚。要是这条街的每一家店都学着做一个就好了,那样我就能即使在雨天不用带伞也不会被淋成落汤鸡。我这么想着,不知道为什么在猪肉包子里吃出了奥尔良鸡肉的味道,随着嗷呜一声惨叫,我才意识到咬到了自己的肉。如果说人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就能获得一个倒霉徽章,那我应该能成为一个在衣服上挂满赫赫战功的人。文具店老板坐在他的小板凳上望着雨,看起来就像是世外高人,能够用手摸着胡子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说着吴语,喝茶。不过他的白色背心显然看起来有些年代感了,而且那羽扇就像是三国时代诸葛亮使过的留到了现在,羽毛已经被历史过滤掉了。这样的老板,如果用“马克笔”三个跟他交流,能够得到回应吗?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上,被老板郑重地交到手上的马克笔陷入沉思,虽然马克笔有蓝色,但这个蓝色好像是比水彩笔更不健康的蓝色。我拿出来嗅了嗅,脑海中想到了:最先想到的是我的头皮,这就是我被雨打了一拳的头皮的感觉吧;我要是拿它画到头皮上,我为什么不把它画在脸上呢;阿凡达就是通过蓝色的马克笔量产的吗;一个阿凡达多少钱;我也能成为阿凡达吗;阿凡达如果在雨天打篮球会变成普通的初中生吗?
老板还坐在门口看雨,我问了句“多少钱”,脑海里突然又响起来了一句“How much is it”,我怎么不说这句呢?要说我能突然说一句英文,老板会不会以为我是外国人。结果老板完全没有回头看在店里的我,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五块”,然后又开始不间断地扇扇子,机器人——一定是机器人。我想了想这种不健康的味道和水彩笔相比,我觉得还是更强大的不健康的味道更好。等我把钱付了从店里出门,店里又响起了电子播报的声音,和老板的扇扇子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是在同一个程序里设置好的。
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同样落汤鸡的初中生,不过跟他相比,我好像看起来更落魄一点儿:左手拎着一袋被水泡着的包子,右手手里拿着一只沾着水的蓝色马克笔。不说身上全淋湿了吧,我的引以为豪的刚睡醒的蓬松的头发,现在紧紧贴着我冰冷的头皮,刘海一把抓住了我的脸,却又很贴心的帮我把眼睛的视线空了出来。他身上披着校服外套,但身上也几乎淋湿了。这时候“年轻”又变得没那么好了,妈妈喊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头顶随着楼道的墙壁一层层的撞击回响越来越近,他的脚步显得又没出门的时候那么坚定了。我开了家门,灯还是关着的。看来出去的时候有好好关灯啊。
好了,该画画了。虽说不健康,但马克笔的墨水像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泉水,而且可以单支购买。我回到房间,透过窗户看,雨仍然把天染成了灰泥鳅般的样子,随着太阳消失不见,灰的纯度再不断增加。用不了多久就会到夜晚了吗?果然效果只能明天再看了,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好像是有点饿,或者是包子确实很好吃。我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准备用马克笔把窗户涂上蓝色。正要从左上角开始落笔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了共享单车被涂得满满当当的二维码。与其被完全覆盖,不如留些信息吧。于是我在两个窗户上分别写了“蓝”“色”。这个字体,如果交给文具店的老板或者能写的更好一点?不知道美术老师现在是不是还在兢兢业业地上班呢,我现在的人生也是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手法,不知道能不能传达给她,再让她笑一笑呢。
带着雨的包子味道好像也不差,不健康的味道要是闻多了,还挺亲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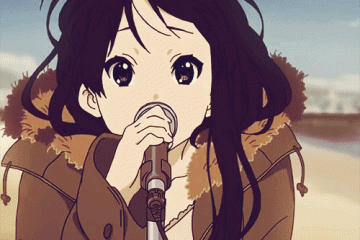


0 条评论